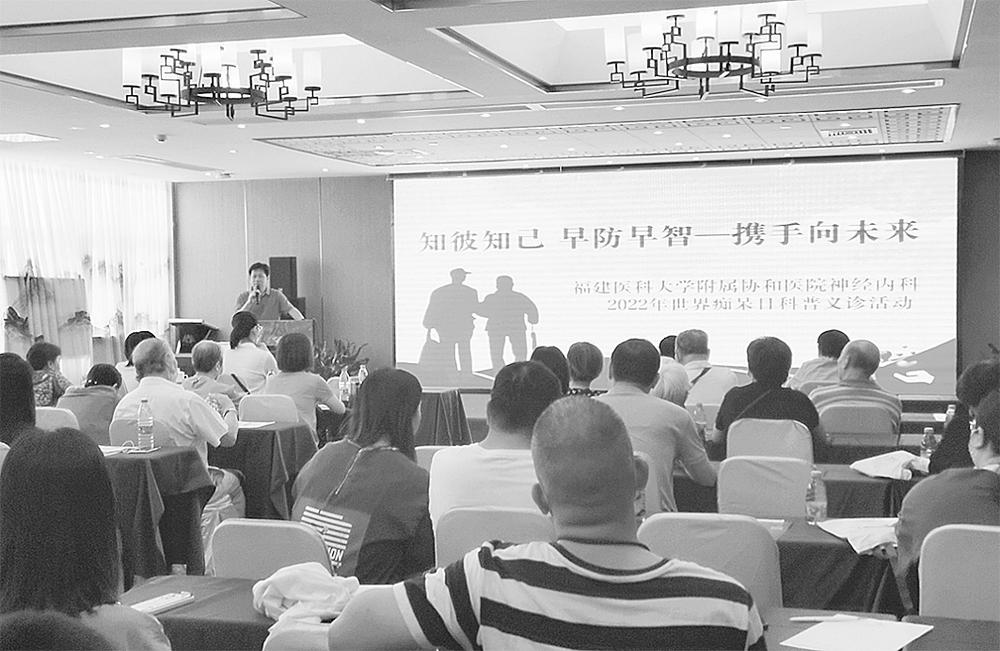3秒钟,伸个懒腰,喝一口水,望一眼窗外的时间,也可能有一个人正在从世上“消失”:失智、失用、失认、失语……据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发布的报告,全球每3秒钟就会产生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照料者来说,除了要照顾患者的饮食起居,还要承受病人出现的以上行为,尽己所能,像海绵一样吸收疾病带给病人的情绪起伏,直至他把这些全部遗忘。
每年的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专家呼吁,除了认识疾病,也应建立完善的社会照护和支持体系,降低照料者负担。
我给妈妈当“妈妈”
近期,电影《妈妈》催泪上映,引发不少网友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关注,电影讲述了一个深受阿尔茨海默病折磨的65岁女儿和照顾她的85岁母亲之间发生的故事。
在现实中,张女士成为73岁的妈妈的“妈妈”。
2017年,张女士发现妈妈常常在小区里迷路,她马上警觉到情况不对,第一时间带妈妈去看了医生。经过检查,妈妈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
张女士在福州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妈妈常住老家又不放心。张女士一咬牙,在小区里买了一套房,把妈妈接到福州。两个家庭既保留独立的空间,又维系着“一碗热汤”的距离。从那以后,张女士开始变成了妈妈的“妈妈”。
除了定期和医生沟通,积极尝试各种新药,张女士还把妈妈的日子尽力拉回轨道。
妈妈得病后,变“蒙”了,没了时空概念,有时候可以睡上一整天,为了让妈妈作息规律,张女士就定了闹钟,上班前准时喊妈妈起床;
妈妈得病后,变“傻”了,每天,张女士都会把药物备好,放在固定的地方;
妈妈慢慢地变“脏”了,不愿意洗澡,她就把妈妈的换洗衣服备好,推着她去洗澡,换上连衣裙;
妈妈得病后就变“懒”了,张女士给她找活干,让她给全家织毛衣,而且都是红色的;
妈妈得病后变“空”了,不再是那个有主见的妈妈,喜欢热闹。于是,张女士坚持每年的全家旅行,即使扶着妈妈走完全程,也要让家人热热闹闹地陪在妈妈周围,让她做一个开心快乐的老太太。
5年的时间,妈妈的认知水平仍维持在轻度障碍。医生也认为十分难得。
张女士说,她很清楚人生大事的排序,比起工作、子女,父母永远排在第一。她一直记得一位作家写给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妈妈的信中的一句话:生命从不等待,此生唯一能给的只有陪伴。
“妈妈的生命已经开始倒计时,未来,她有可能不记得坐在对面的我们。听上去很悲凉,但也让我想用尽全力爱她。庆幸的是,她的记忆是从最新鲜的开始消失的,从73岁退回3岁孩子的记忆。我要拉住时间,让她记得我们的日子再多一点。这一次,让我来当妈妈。”张女士说。
“我是独生子,真的害怕
最后那一天的到来”
像张女士这样,能体面地照顾阿尔茨海默病家属的例子并不多见。
福建卫生报健康大使、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叶钦勇告诉记者,超过一半的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在5年内会进展为痴呆,其中大部分类型为阿尔茨海默病。不少家属发现亲人得了认知障碍,就陷入悲观情绪,认为得了病就只有“一天比一天傻”的结局,直接放弃就医。
养老院的费用也不小:据了解,福州招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养老机构,一个月收费一般在4000元~1万元不等,且根据病人精神症状评分和护理等级、照护条件的提高,费用还会相应增加。
很多患者家属舍不得把病人放养老院,又缺乏照护知识,一边帮病人把屎把尿,一边还要忍受着患者因病情带来的易怒、暴力,甚至对亲人的淡漠和遗忘。
目前,我国65岁以上人群的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率为5.6%,85岁以上人群的发病率高达40%。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来说,家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有资料显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往往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治疗照护,照料者平均每周需要放弃47小时的工作时间(相当于6个工作日)来照顾患者。
然而,患者家属往往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照护技能,在承担长期的、高负荷照护的同时,还要设法应对患病亲人可能产生的异常情绪和行为,其间的艰难程度难以为外界体会。
在福建卫生报阿尔茨海默病病友群,有一位病友家属就曾提到自己患病的妈妈:经常丢三落四,脾气暴躁,东西用完了不放回原位,等找不到时会大骂儿子。一周几乎有5天,因为找不到东西,去单位找儿子,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他在群里感叹:我是独生子,真的害怕最后那一天的到来。
研究表明,有20%的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照料者罹患忧郁症,有65%的人具有抑郁倾向。
福州市小蜜蜂扶老公益服务中心主任陈瑶常年组织针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公益活动。她告诉记者,经常有患者家属通过网上搜索到的电话号码联系她,向她倾诉,某天半夜,病人又不睡觉。家属只能强撑着陪着,白天快崩溃了。
2016年,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发布了《中国认知障碍患者照料管理专家共识》,对中国的认知障碍患者照料者提出指导建议,同时也提出,认知障碍患者照料者要进行科学的压力评估和调适。
(下转5版)